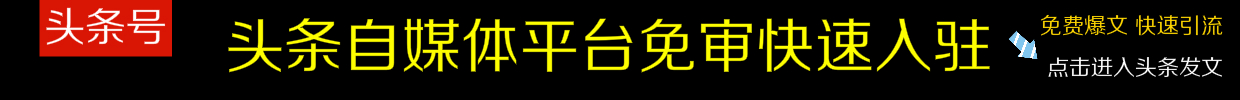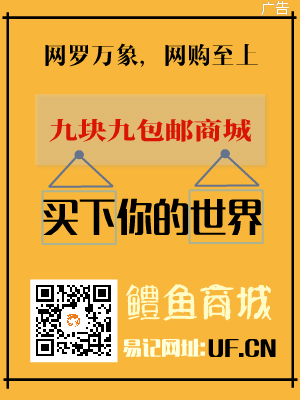提起油画,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它来自于西方,是富有激情且多彩的艺术,从七世纪开始阿富汗人就用油画颜料绘制,传入欧洲后就出现了多样的艺术形式。
 (资料图)
(资料图)
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三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又创作出叫做坦培拉的类似油画的艺术手法,从起源直到今天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然而时代的车轮不曾停息,它改变着世界,也牵引着艺术的发展。油画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古典、近代、现代几个时期,不同时期的油画受着时代的艺术思想支配和技法的制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20 世纪油画中,由不同的艺术观念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并制约艺术形式呈现出多种倾向,传统油画技法中的某方面因素往往作为艺术观念的形式体现被强化甚至被推向极端,油画形式语言受到高度重视。随着艺术观念的不断扩大,导致油画材料与其他材料相结合,产生了不归属某一具体画种的综合性艺术,油画因此也走向失去在西方作为主要画种的地位的趋势。
中国传统绘画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更是我国五千年文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珍贵的历史价值,它包罗万象,承载了对天地、哲学、人生、自然的思考和理解。书法和绘画是中国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诗、书、画、印完美的结合延续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以墨为线,追求 神似,注重意境,气韵生动的中国画从起源至今至少已有七千余年了,它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中国画从原始岩画到当代中国画,“写意精神”贯穿始终,强调的是意存笔先,画尽意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在画法上运用骨法用笔,比比生发,气韵生动,见笔见性。笔力由骨气达, 无骨则无势。中国画力求以笔见势,以笔见趣,以笔见情。吴悦石先生说:“笔韵是中国画大写意的灵魂。气为阴,以笔为形,重在显力,韵为阳,水墨为道,重以显柔。韵者,音匀相合,表现悠扬旋律,绵长,回味无穷。欲得气韵生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水和墨用活,掌握水墨渗韵的巧妙之处,中国画的特点就是把笔墨的韵味画出来。”“西画重形中国画重势。”
油画是从很晚才进入到中国的,而且它进入中国的方式也带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冲击性。油画的色彩更鲜艳,饱和度更高,色彩的变化也更丰富 ,画面厚堆 ,可见笔触。油画的进入与所有的外来文化进入华夏文明都有关联 ,它必然会和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以及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相结合。所以在绘画题材上都是中国式的,中国的风景,中国的人物,而且会在自觉或者不自觉中,掺杂一些中国式的情怀。国画都是平的 ,都是画在一个比较平面的纸本上,或者绢本上的,对绘画过程的要求精细,有些作品中笔头末端的变化,是国画审美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在作画时,一笔下去,它的浓淡干湿,皴擦点染,全都带有审美的节奏和倾向。
鲁迅先生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何在油画的画布上传递出中国画特有的写意精神,如何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神韵体现在西方油画媒介上,一直是我们需要不断探索与追求的方向。为此我采访报道了一些油画艺术家,在采访中我充分的感受到,当今很多艺术家在传统意象与西方艺术语言中寻觅,找到了一种新的语境。比如在徐里先生的油画作品中,我看到他在保存油画色彩肌理的同时,把中国画的笔墨点线转化成油画的笔触,把中国画山水图式的象形与布置的虚实留白转化为油画的意向与构图,把中国画的笔墨气韵转化成油画色彩的和谐交响,形成了浓郁的中国逸趣、中国境界、中国气象、甚至隐含着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虚实相生,有无象形的中国哲理。随着八五思潮后以西方写实油画和现代艺术的后殖民主义思潮对中国画产生的巨大冲击, 徐里先生的画学思想从“民族性”的外在会通转向“价值论”的内在超越,回归到中国本土绘画重内在精神和写意形态的价值挖掘和自觉维护,而其艺术实践的多样探索和丰富形态,也体现出了对于古今承变和东西的贯通,所以徐里先生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融合改良派”,而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最早具有开放艺术视野和“文化自觉”的先行者。
徐里先生的作品《山有梯田坝有海》,虽然画面表现是具象的,但里面融入了很多中国元素,中国画讲究留白,这幅画在表现天空时,三分之二的空间都是留白,在留白的过程中又充分体现着油画的元素,光的感觉,形成雾气蒙蒙的山区景象,画梯田时又把中国画的线条线性比较概括地表现出来,所以这幅画既有西方的光影效果,又有中国画的简约,概括,留白和意境的元素。
还有徐里先生的作品《天长地久》, 就把希腊的、埃及的、 还有藏族的艺术辉煌都融为一体了,走民族化的道路。他去了新疆、西藏、敦煌等等地方采风取材,还吸取了很多的民间绘画和民俗的元素,把东方绘画文化的元素例如古印度、古埃及这些绘画的表现手法以及中国的这种线条融入在作品之中。《天长地久》这幅作品的肌理效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算是比较新的处理,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还不太会做肌理,通过肌理效果,再运用中国的线条,加上壁画式的表现手法来呈现出作者所想呈现出的内容,而且徐里先生表现出了它那种原始的表象和藏民族的和谐、包容与豁达。
民族审美心理是民族文化的结构、性格等特质在历史发展演变的长河中,受制于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徐里先生一直关注探究民族审美心理和审美结构对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行为的影响,以便客观真实地理解中国传统的“意象”精神在西方油画本土化,民族画过程中的构成表现以及西方客观写实在中国画发展融合的过程中的语言转换。徐里先生在艺术上表现了水墨借古开今,有着凛然不可犯的壮怀豪情,气足神旺。又如谢岩自幼和父亲学习中国画,所以画国画比较多 。但是从进入专业训练学习开始后 ,才慢慢逐渐在学习当中转向了对西方美术的学习。谢岩的作品既保留了水墨晕染的淋漓效果,蕴含着借景抒情的文人情怀,又将油画饱满的颜色呈现于世人面前。他在中西结合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将中西方艺术文化的观察、比较和讨论作为他绘画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谢岩的作品中,无论是中国画还是油画都笼罩着一层东方意蕴,比如作品《水何澹澹》,所有的景色都概括为两种意境,画面被分割为三块抽象的形,树木不再是树木,倒影也不再是倒影,近处的枯荷像一串轻盈的音符,墨色荡漾,漂泊浓重的笔墨勾写出美妙的吟唱。
以艺术家们几十年的绘画观念的发展变迁去分析同时期中国传统绘画在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下自身所发生的变革,不仅梳理了艺术家作为个体的自我风格、观念的演变进程,也树立了中国绘画观念的变迁脉络,在这一番变迁过程中,一直伴随着纷争,如何正视西方绘画观念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如何发挥中国绘画传统中的精髓,直到今天仍是中国绘画发展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还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美学意识融入到油画创作中,用中国传统的写意精神来“观照”西方油画艺术,在研究中国传统绘画的同时,结合西方油画材料特质,并融入中国传统绘画对审美意境的追求。中国绘画的过程,虽然不像西方变化那么剧烈,但实际上也一直在缓慢地,不断地革新,其实每一个变化都是一个创新,都是巨大的社会进步,也是文化进步,当年一个小小的创新,从一千年以后回头看它, 我们会觉得它是璀璨的传统文化。如果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还想继续坚持下去就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走,只有创新,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才有生命力,才会真正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支脉和源流。
过去是现在的传统,今天是明天的传统。时代牵引艺术的发展。当以往的规范和审美标准不能满足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时,大胆对传统油画进行当代转换便是现阶段 “中西融合”艺术创作的一个前提。中西油画各自成体系,各有各的发展规律和独特的文化背景,正如潘天寿先生所说,中西绘画“就如两大高峰,对峙于亚欧大陆之间,这两者之间尽可互取所长,以为两峰增加高度和阔度,这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