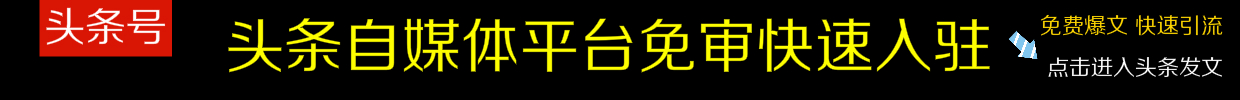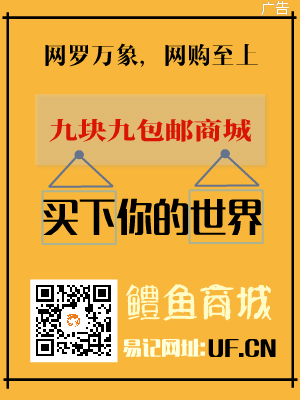11月5日,未名医药(002581.SZ)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下称“厦门未名”)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1)京民终34号《民事判决书》,2022年10月31日,北京市高院出具终审判决,维持北京四中院的判决,对于未名医药方面因为拉电闸给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称“北京科兴”)造成的疫苗产品损失,赔偿1540.4万元。
这意味着,开始于2018年的北京科兴生物控制权争夺战,未名医药输一局。
一输再输!“拉闸”一方被判赔1540万元上述事件缘起2018年4月17日,北京科兴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39号的办公楼及厂房的电源,被通过位于同一地址的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配电室的总控开关人为切断,造成北京科兴疫苗产品共计市场价值1540.4万元的损失。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电源被人为切断后,北京科兴的控股股东科兴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称“科兴香港”)将未名医药、厦门未名及潘爱华均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
其后,据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曾于2020年9月17日出具的《民事判决书》,认为该起事件起因是厦门未名与科兴香港关于北京科兴控制权存在争议。当时,潘爱华是由厦门未名委派担任的北京科兴董事长。因此,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厦门未名、潘爱华向北京科兴连带赔偿损失1540.4万。
据未名医药2021年年报,公司曾在2021年11月12日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诉讼,原因是:
科兴香港子公司北京科兴在疫苗研发、临床试验过程中将北京科兴的人员、技术、设备等资源不断输送至科兴中维,厦门未名要求科兴香港、科兴中维等连带赔偿北京科兴损失2亿元。
就上述断电事件,最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同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未名医药未参与上述断电行为,且非共同侵权人,但在侵权行为发生时,厦门未名的唯一股东是未名医药。
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厦门未名不能完整、准确反映与未名医药之间的财务往来,不能证明厦门未名财务独立于本公司,因此,未名医药也应对厦门未名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未享受到北京科兴生物红利,却先赔了一笔钱,对于业绩不佳的未名医药并不是好消息。
根据未名医药的三季报披露,从营收到净利到现金流,全部下滑。2022年前三个季度营收近2.76亿,同比降12.75%;扣非净利6000余万,同比降82.36%。
所以未名医药在公告中称,连带赔偿预计将对公司当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争斗近5年未名医药索赔两亿这起案件中涉及的不仅仅是潘爱华断电,还有对公司控股权的争夺,以及一些陈年往事。
公开资料显示,北京科兴是由香港科兴、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合资组建的生物高新技术企业。香港科兴的控股方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兴生物。
未名医药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司持有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26.91%股权,未持有美国上市公司科兴生物股权。
2003年中外股东签署《备忘录》约定保持中方股东在北京科兴生物董事会的控制地位。至2018年2月26日之前,北京科兴生物始终按照备忘录确定的公司治理机制运行。
据未名医药2021年报披露,2018年2月27日,外方股东在中方股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面更换董事,破坏北京科兴董事的委派规则,致使公司的运行机制失灵,公司陷入僵局。中方股东游离于北京科兴之外,不能基于其投资享有公司经营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股东权利,股东权益受到重大损害,中外股东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利益冲突。
未名医药称,科兴中维设立的目的仅系作为医药研发企业。但随着新冠疫情爆发,科兴香港在新冠疫苗研发、临床试验过程中,将北京科兴生物的人员、技术、设备等资源不断输送至科兴中维,并且通过变更科兴中维经营范围、将新冠疫苗车间建设项目建设主体由北京科兴生物变更为科兴中维等方式,使科兴中维变成与北京科兴生物经营范围基本一致的集人用疫苗科研、生产、销售于一身的医药企业,以获取新冠疫苗销售利润。
2020年10月20日,尹卫东和SVA创办科鼎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下称“香港科鼎”),作为其从科兴中维获取利益的平台。
2021年2月5日,新冠灭活疫苗克尔来福在国内附条件上市,但申请方仅为科兴中维,北京科兴被完全排除在外。未名医药称,根据公开渠道公示的数据推算,仅2021年上半年科兴中维因新冠疫苗盈利即已超500亿元。科兴香港方面的侵权行为,已造成北京科兴生物巨额经济损失。
2021年11月12日,厦门未名作为主体起诉索赔2亿。3天后即11月15日,再次起诉要求解散北京科兴生物。至今法院尚未开庭。